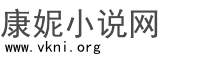佚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康妮小说网https://www.vkni.org),接着再看更方便。
灵牙,三山林公得山居士所施也,居士得是牙于燕京古寺中,纵六寸、广五寸有奇,重七十八两,其大龈如金,细齿如玉,坚好香洁,盖是过去古佛大牙,实希有之灵踪也。舍利,昔宜兴曹安祖居士于崇祯甲戌间,监军中州,因流寇侵境,取通许县洪福寺圯塔修城,至第四层,得一石匣,启之,中有水晶瓶七,俱贮舍利,银瓶一,中贮佛骨一节。舍利如黍者甚众,考之旧碑,系宋仁宗皇佑元年,太后曹氏命中官取宫中所有佛骨、舍利藏之于此。时当事者遂各持散,曹公得其一持归,拟建塔于邑之南岳寺,以病弗果。临易箦,付槜李曹愚公居士,居士转付先师。先师既以原瓶建殿,立塔于宝善庵,乃复分其半来鼓山,巨细共计七十八粒,贮以沈太树所施之晶瓶,亦拟建殿塔,以启四众福基。第以时事多故,未及就绪,道霈勉承遗意,乃命比丘太靖、等照、兴宣募化富沙,温陵,庆元、寿宁众善信,于净业堂之前,鼎建正法藏殿五楹间。始工于己亥之冬,落成于庚子之秋,共费金钱若干。殿堂廊庑,黝垩丹青蒦,无不如法。左右安奉二《藏经》。比丘道悟、寂影、化清、信弟子陈寂知,王法龄共造石塔一座于殿中,以供灵牙舍利,皆一时缘起之功,例得并书,以传于无穷也。
是举也,使凡登斯殿,礼斯塔,翻阅斯藏者即是于灵鹫山中亲见如来,谛聆妙法;亦是亲见自己,更无凡圣之隔,自他之殊,所谓三际一时,因果一致者,于此可概见矣。方知如来常住,真身本无出世及与湼槃,虽随机示现,但如镜像水月,何莫非自心之光影?愿诸来者幸毋怠斯旨,庶不负众居士檀施之功,与诸比丘勤劳之力耳。或有问于予曰:“此殿不以舍利名,而名正法藏何也?”曰:“为法藏所发起也。”抑予尝考之:舍利有二种,一法身舍利,三藏十二部是也;二,生身舍利,灵牙珠子是也。然则法藏即舍利,舍利即法藏。标法藏,舍利在其中矣。问者唯而退,因并记之云尔。
顺治十七年八月,住山道霈记,监院成源立石。
————乾隆《鼓山志 艺文》
重建白云廨院疏
鼓山之麓有白云廨院,创始于闽王审知,用以安行僧,辨道粮,与接纳云水宾客之往来,实涌泉之化城也。迨今余七百载,沧桑屡更,因革不一,旧有三门、佛殿、法堂及两游廊,岁月既久,柱根腐坏,栋宇差脱,岌岌然,过者疑将压焉。而僧之隶是者,又为残产所累,日收租输官不暇,况能修葺院宇哉?坐是,败屋颓垣,满目荒榛,大约如逃亡人家。客岁,住僧又化去,而院益无主,由是,护法方公克之率众护法及诸善信以残田累僧者,乃援旧例,充送入官,而院始清脱,复归上寺,且捐金为倡,谋鼎新之。
予惟天下之事,缘会则兴,缘离则废。废兴固若靡常,而亦有数存焉。廨院与涌泉、判而为二也,不止百余年。至于今日,粮产荡尽,住僧凋落,金像蒙尘,殿宇崩塌,废可谓极矣。然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故又得方公及诸护法同诸善信、殚力恢复,合二院为一,以还旧观,谓非当今之会乎?但所费不赀,独力难举,用是谨持短疏,仰乞檀门,且佛法常住世间,则布金给孤,插草帝释,岂无其人?但施藏一启,则胜因自然成就耳。况一粒一文无非福田嘉种,信地灵苗,因果历然,终不虚也。
————乾隆《鼓山志 艺文》
朱彝尊生平见《词》。
鼓山题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东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郑埕,乘竹轿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而行松阴三里,达涌泉寺。寺创自梁开平二年,闽王审知所建,延国师神晏居之。入门,山僧迎客,饭香积厨,寻挟之出探灵源洞,下岩磴数十级,中裂一涧,跨以石梁,下视乏水,山僧语予,“此喝水岩也。国师安禅于是,恶涧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涸。”予为怅然。旁多宋人题字,有徐锡之者,刊诗于石云:“重峦复岭锁松关,只欠泉声入座间。我若当年侍师侧,不教喝水过他山。”辞颇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郑子登屴崱峰,予纳凉僧廊,日既暮,留憩廊下,爱青松架壑,信宿乃还。用苕帚拂尘,题名于壁。
————《曝书亭集》卷六十八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高兆字云客,号固斋,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崇祯间诸生,入清曾一度附耿精忠,以布衣终。他在当时是一个名气很大的文人。与毛奇龄、施闰章等均有深交。
千佛庵记
岁戊子,先府君既营生圹于凫屿,自题其碑曰:“高公真隐”,日来往丛林与诸长老游,一日遇蜀中行实□公于途,破衲苍颜,提竹筐俯拾字纸马通中,揖而询之,云:“二十年矣。”明日延于家,居以草堂右轩,行公有友九达宗公,故涌泉监院,真实大德,先府君爱重之如行公。久之,念行公老,为谋退居地,宗公云:“涌泉之右,有洞曰达摩,石屋山园,足以栖吾友。”于是先府君与先安人捐捨私钱买置。时行公行愿未毕,达公适辞监院之职,先府君乃属宗公居以待之。亡何,行公偕先府君侍空隐禅师游古灵归,渡江示疾舟中,不果居。明年庚寅,宗公以其地狭隘且瘠,相其东偏,得无诤三昧大磐石,其阴平坦,来谋于先府君,徙其宇,益以左右楹,稍治松下隙地,种茶蔬,辛卯落成。永觉禅师来过,喜之,曰:“石书无诤居,斯名之矣。”越三年,先府君捐馆,又十三年,宗公手凿层岡,己日平衍,屋后松竹已长,山坳且成畎浍,于是拓屋之堂为殿,翼楹为寮,庖湢井舂之庑,无不次举;又大造毘卢千佛,像设庄严,钟鼓镗镗,复以余力镂镌大乘,易居之名,曰:“千佛庵”。庵甫成,心力亦瘁,遂以丁巳二月,示疾化去。宗公殁之先一月遇予,云,“宗已衰老,请举此庵并所辟田施诸常住,公为我作记,留示山中。”予伟公斯论,谓公精神尚固,姑唯唯。未几日,疾作且殁矣。宗公既殁,门徒太瀛来赴丧,予与四众则留瀛公主庵事。瀛公者自童子执侍,长出参方,得法南归,隐九峰,固先府君所见有志之士也。
越四年,予入山,瀛公请曰:“庵之记,公许先师矣。逝者复四易寒暑,公安忍忘之?”予惟庐舍田园,守成百世,此愚夫子孙之计,非所论于道人。是庵也,溯自行公以来,三十有二年耳,一徙其地,两拓其宇,三易其名,庵之宾主,无复有存,存者惟予与瀛公矣。予又将老,人生何物,是为常住,更二十年,瀛公亦六十。瀛公他日能成阿师末后之志,副府君买山之意,则兹庵可以记矣。
————《春霭亭杂录文稿》旧抄本
题鼓山僧赠黄学庵检校□后
乙未六月十六日
十年中予入鼓山不一,或一岁再至,或隔岁一至,山中麋鹿皆相识,而僧则有识,有不识者。麋鹿以余来往故识,僧则以予所共游之人,为识不识,故不相识矣。学庵仪曹今夏入山,慮僧不识之,索吾儿八行往。予归知之,语儿曰:“儿误黄公矣,以黄公苍然伟岸之貌,山中人见之必疑,疑则必将迎接待,徐叩姓氏,群聚而奉教焉。使出儿札,误黄公矣。”阅月,学庵还,持山中僧赠诗一卷示予,予喜僧能识学庵,而学庵尚能使僧识,三诵其诗。学庵曰:“予入山投君儿之札,僧不发函,曰:‘此僧他往矣。’数日,昇稍稍以篆文与语,又越曰,昇作篆,篆成,应接不暇,煮清泠之泉,设蔬笋之供,惟昇饥渴是视。比昇归,挽留坚固不许,则倾院出送千松万壑间,杖笠之影行廨院石桥,尚依依不捨去。”予顾儿曰:“予以黄公必有以动山中人之心,果然也。儿几误黄公矣。”嗟乎!学庵之篆如予所挟游之人,所挟游最胜之人也。山中人有不识学庵者乎?今而后学庵即隔岁不至,一二十年不至,无有不识学庵者矣。第恐学庵为僧所苦,未出尽泉石之兴,他日麋鹿未必识学庵。
————《春霭亭杂录文稿》旧抄本
兴隆福建莆田人,幼业儒,年二十五,游鼓山,依恒涛和尚出家。后结茅天台,清乾隆九年(1744年)回福州,十四年(1749年)为涌泉寺住持,修建殿堂,重整山门,为众所信仰。世称遍照禅师。
募修涌泉寺疏(时辛未年)
天下名山僧占多,非僧占也,僧特为十方名贤、名士守此名山耳。所以者何?地方风水之盛衰,由于形胜之废兴,而省会所关尤钜。吾闽领郡十,州二,福称首。西北倚山,东南际海,登样楼一览,九峰如列屏,五阜如展案,左鼓右旗,洋洋乎大观哉!四山周密,轮廊迥环,独巽方微缺。昔人砌塔江心,作水口罗星似矣,而不知天地自然之补苴,已实具于石鼓山中,所赖有心培植者,时时加之意焉已。
鼓山发源千里,拔地千寻,松杉葱蒨,障蔽长空。屴崱峰岿然屹立,涌泉寺实居峰际。五代晏国师开山以来,祖灯法席,屡废迭兴,一千余载。其间名公、钜卿修饰题镌,更难仆数;若名宦赵公“天风海涛”之句,先贤朱子“闽山第一”之书,尤彪炳者。入本朝康熙间,勅赐御书匾额,钦颁御藏十厨,崇奉高悬,人天钦仰。蒙前制府郝公倡缘,率当事诸宪,捐田六十亩,所以珍护名山者,至周悉矣。历岁祝国焚修,競競顶颂,无非为十方名贤、名士谨守此名山也。去秋霖潦连旬,飓颱屡发,山高寺古,罹害尤剧。贫衲蒿目飘摇,侧身呗颂,大有侨将压焉之惧,宁尚敢漠然作秦越人视乎?用是普请十方善信、宰官、居士随缘乐施,择吉重修,广种胜因,定圆福果,庶弹指告成,圣祖天章永焕,众擎易举,昔贤胜迹长昭,则省会之形胜既雄,全闽之风水鼎盛矣!
然贫衲尤愿十方名贤、名士,同心协护名山,无讶山僧祗为我佛如来筑舍道旁,谋久占也。幸甚!幸甚!
————乾隆《鼓山志 艺文》
鼓山志序
鼓山自唐灵峤禅师以诵《华严》徙毒龙,郡从事奏请立寺,赐名华严,实开山之鼻祖也。五代梁开平二年,闽王审知具百戏、香花诣雪峰,延神晏法师,始乃洪开丛林,大转法轮,食常万指。宋真宗二年,赐额“白云峰涌泉禅院。咸平二年,赐御书一百二十卷。皇佑三年赐御书二轴。至和元年,赐《新乐图》三卷。国朝康熙三十八年,勅赐御书“涌泉寺”匾额。五十三年,又赐御藏四橱。乾隆七年,赐御藏七千二百四十卷。晨昏诵祝,朔望呼嵩;且名贤之探奇岩阿,镌刻石壁,其胜迹流风,岂可任其湮没而不志哉?
兹山古无志,明永乐间,住山善缘裒《灵源集》始。万历戊申谢方伯(按指谢肇淛)与布衣徐兴公再为纂辑。国初,永觉老人以真儒度世,复承徐兴公以续稿见付,志乃大备。迄今百余年已。隆驽钝固陋,承乏住持,十有三载,每思黾勉续修,奈缘时事不偶。戊寅春,制府杨公(按指闽浙总督杨应琚)以劝农之便入山,问国朝勅赐御书藏经曾编入志不?隆惭谢无以对。由是录文献,剔苔藓,搜古今名贤之遗文剩字,弥月稿就。延郡绅纂修,三年编葺成书。山僧一言莫措,惟汲汲典缾钵,锲枣梨,窃自幸曰:“永祖百余年不了之公案,今日完矣。”昔有客得孙知微活水遗法,绘画浪于壁间,于三伏溽暑时,坐一堵之间者,须曳足江湖万顷之势,壮波怒涡,洼窿千状,而有不穷之变。阴风徐来,毛骨震掉,忽然如舟洞庭,而望霜晓也。睇兹新编,神与境会,不移跬步得与苏才翁、赵子直、朱晦翁、蔡端明诸君子,把酒吟咏于天风海涛、忘归、喝水之间,仰瞻宸翰御书之辉煌,玉轴瑶函之广润,庆喜见阿闪佛国,岂可思议乎哉!
时乾隆二十六年、岁次辛巳、端阳日,现住鼓山沙门兴隆叙。
————乾隆《鼓山志》卷首
李馥(1661~?年)字汝嘉,号鹿山,福建福清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人,官至浙江巡抚。为人和厚谦谨,藏书甚富,乾隆九年(1744年)重宴鹿鸣,时年八十四。
请遍照禅师住鼓山疏
伏以毒鼓雷轰彩映,伽黎金缕艳,石门狮吼光摇,柏子宝花生。月惟智而常圆,即心即佛,云垂慈而遍覆,是色是空。故净土为彼岸之登,弹指亦传灯之偈。大千世界,现出三玄三要真世尊;不二诸天,请个一钵一瓶活菩萨。
恭维遍公大禅师,智空丽象,慧现金客,嗣恒和尚之正宗,阐为老人之真谛。批风抹月,处处山色溪声;飞絮沾泥,点点天花散雨。蒲团面壁,何止九年?般若参玄,已通五乘。
兹者鼓山涌泉寺、十郡无双巨刹,三山第一名蓝。地辟尊严,道开兴圣。半天钟磬,蒲牢月落长江;万磴松筠,棒喝泉归别涧。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殿上维摩见了今今古古;甚么闻,甚么见,甚么觉,心头佛火照到万万千千。法有盛而无衰,寺必兴而不废。奈飞空掷锡,近留绀室袈裟;喜顽石点头,同奉云堂领袖。上莲花之座,开贝叶之台。说法山中,五百阿罗汉齐来拍掌;讲经松际,百千大头陀尽向拈花。灵源出洞,新振法雷;屴崱登峰,重开慧日。庶大拳小指,长看佛国之菩提;暮鼓晨钟,永奠山门之昙缽。馥等俗缘未了。安知水印瓶中,至教难闻,谁悟云在天上?但遥瞻宝盖,如游鹿苑而洗尘心;翘望珠林,恍入鹫峰而生净念。齐钦宝筏,普庆慈航。谨疏。
————乾隆《鼓山志 艺文》
黄任生平见《诗》。
鼓山志序
历代志乘,递相沿袭,莫不各有所仿。《三秦》、《三辅黄图》、《决录》之属,仿于班氏之十志也。《十洲》、《洞冥》、《真腊》、《佛国》之属,仿于《山海经》也。自是而支分派别,一地、一事亦各有著述,《洛阳伽蓝》、《建康宫殿》、《襄阳耆旧》、《汝南先贤》虽尺帙寸楮,亦蔚然自成一书。迨庄、老退而山水滋,于是有《寰宇记》,有《名山志》,有《名胜志》,莫不发宇宙之瑰玮,而聚山川之秀灵,览者可卧游而得焉。
吾闽之鼓山,去城三十里而近,至唐而始显。僧神晏象教继兴,宋苏才翁、蔡君谟、朱晦翁诸君子各有题味,而名人韵士之流连景光,发为歌吟者,又不可以计数也。然则山志可任其残脱不修乎?
考旧志始末,僧善缘著《灵源集》,黄用中改为《鼓山志》,后谢在杭、徐兴公、僧元贤相继纂辑,及今复百余年矣。旧板漫漶不可辨,记载亦未备。住持遍照和尚出元贤旧志,乞余续而成之。因细为编阅,于旧志之逸者存之,繁者汰之,讹者正之,疑者缺之,不分纲目,统别八类,非故立异,究亦何必尽同?
书成,私自喜曰:“八十衰老之身,不复能杖履,作谢康乐之游,犹得从几帙之余,如躬履其地,挹屴崱,灵源之胜于缥缃砚席之间,山灵其不我遐弃耶?
前者山寺颇颓废,遍师有重开忄刃利、再振精蓝之功,余论志不必评书。
乾隆二十六年蒲月,郡人黄任,时年七十有九。
————乾隆《鼓山志》卷首
徐景焘字璞斋,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清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擢庶吉士,十五年至十九年(1750~1754年)任福州知府,曾编纂《福州府志》,官至盐法道。
仰膏序
乾隆辛未夏,郡中弥月不雨,陂堰将涸,秋稼难殖为惧。于是制府喀公、中丞潘公暨同郡镇守大吏,率厥官属,步祷群祀,旬浃几遍。
去州城东三十里,郡镇山曰鼓山。山之峰最高者曰屴崱。峰之左有洞,秘涧水曰灵源。宋徐鹿卿尝奉郡帅命,祷雨于此而验。六月丙辰,制、抚二公亲撰词具币,命予偕参戎杨君廷栻,窦君宁,知闽县事吴君至慎,布政椽属王君作人祷于峰下,又祷于灵源。越三日,戊午,日既中,礼毕,睨峰西有云,簇簇如奔马。俄顷,蔽翳山谷,雷电晦冥,甘雨大注。余与诸吏人休于是亭,咸以为灵贶昭答,不爽如是。
余谓山川百神,其鉴吾二公精神有素,兹山用能洩云兴雨,以膏我禾黍,兆成丰穰,不疾而速,有以也夫。众以为然,自是连二日雨,农野具徧。
兹役也,斋宿于山中日三,致祷于峰,于源者九。每祷辄有云气栖峰上,既事渐散,是日独无有。然顷之,卒雨,亦异矣。亭去灵源百步,余以得所请,而因偃息于此也。爰忆《左氏传》:“百谷仰膏雨”之语,摘其二言,揭于楣间,以彰山灵之庥,而又记其大凡云。
————乾隆《鼓山志 艺文》
叶观国生平见《诗》。
鼓山住持遍照禅师捐修崇妙石塔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