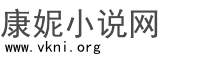佚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康妮小说网https://www.vkni.org),接着再看更方便。
六游鼓山记
庚子正月癸丑,郭子自乌石盥沐,时石鼓在浮云中,而湿衣者已蒙蒙如雨,赵子新、吴子伯敬屡东望而屡转屣。弥陀僧慎修曰:“浮云可以阻游兴,微雨可以限屐齿耶?君辈去岁五游石鼓,皆晴明,缘悭于雨矣。”且行抵山麓,泉声澎澎,霁色澄澄,郭子曰:“是足以悦心目,涤胸襟,资吟啸矣。”转入松际,冈峦之出没,钟磬之浮沈,相继于寺而不绝。忻然乘大小顶,俯长江,瞰大海。吴子咏苏子由“远山如伏羔”句,郭子曰:“是善状登高者,灵源般若山之小壑,人争睹之,何不此之乐也?天下惟勇往者可与造道,而不囿于凡近。向在乌石不知有石鼓,至石鼓不知有灵源、般若,矧大小顶,长江、大海乎?惜缘悭于雨,使屐齿不得奏功。”慎修曰:“欲出喜晴,既至喜雨,心之进退宁有极乎?欲雨旋晴,晴易则雨,亦易天之变化,宁可穷乎?”坐定,浮云如絮入白云堂,而湿衣者又蒙蒙然。郭子曰:“浮云不足以阻游兴,微雨可以限屐齿耶?”以余力游灵源洞,般若溪,慎修绘《春雨携僧游般若溪图》,乃归。
————《葭柎草堂集》卷上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本
按:庚子当系道光二十年(1840年)。
三游白云洞记
洞以险胜,由埔头憩积翠庵,历三天门,转迤而至,往返逾十里。春多雨,夏秋日烈,冬则羸于衣裳,游者惮焉。
道光乙巳春仲,李子希文、季弟柏芗,姪式昌嘱为前导,入一天门,经龙脊道,其石滑泽如瓜皮,上削而旁剡,以手代足。下俯绝涧,行者若着屐登霜桥、雪岺,稍一疎虞,骨辄破碎,至三天门,隘甚,众皆侧度,肥者苦矣。幸有小径,许客子绕行也。喘息间,见巨石突兀空际,僧曰:“洞迩矣。”踏石磴七百余级,磴尽而坪,坪尽而洞,二石如重唇,广七丈,深三之一,就嵌处设槛扉,香火特深邃焉。洞前累石为台,溪光山影,海鸟汀云,不可辨识,惟大桥如缕仆地,七城直一团小烟树耳。导僧呼洞僧为菩萨,予丁酉来游,见其拥二巨蟒宿,如抚婴儿。今貌愈古,眉交于睫,方以草茎绽衲,见客不理;但拾生薪煮茶,薪香郁郁,从石罅出,茶熟,味之甘冽,倍于寺,盖吼雷湫也。夫草茎易绝,湿薪无焰,僧若不厌其劳,惟道气胜,故能受苦况,此其所以为修身之学欤?
茶毕,风寒,冥冥欲雨,急左旋,由海音洞入寺,此迩来新辟径也。视埔头略远,而稍夷,然行人亦接臂作猿狖状。人影在重涧中,涧石黝黑如墨,可以取火。举步旋转,三尺之外不辨趋向,前有负米给僧而坠岩者,首纳于腹。予戒同游曰:“至险之地,须以心平气和处之。古人终其身于忧患,而跬步不失。”吾侪于履道坦坦中,偶尔提防亦足以警心目。吾故曰:“洞以险胜。”彼游石鼓者畏登屴崱,登屴崱者畏寻白云,不到白云,不知山骨,而猥以灵源、般若傲人,亦已浅矣。
————《葭柎草堂集》卷上
按:乙巳当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陈模字子范,一字勒生,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清光绪时入福建船政水师学校肄业,后入芜湖海关佣书,与林森、陈其美友善,旋加入同盟会,又调往上海关。民国初,会中人多显达,模佣书如故,并加入南社。二次革命,讨袁军兴,模为陈其美制炸弹,欲刺郑汝成,适侦骑在门,模方掩蔽,弹适发,模被炸死。林森葬其遗骨于杭州孤山之岁寒岩,孙中山书“舍身为群”题其墓云。
重游鼓山记
去闽垣五十里,有山曰鼓山,镇马江之中枢,为城东之屏障。山石荦确,野径纡回,寺观穹窿,松楸疏散。五里一亭,十里一阁,名流觞詠,恒集于此,盖福州第一名胜也。
客岁,余买棹旋里,尘装甫卸,即雇笋舆,向东而行,直穷其胜。时适春和,晴空一碧,山容如画,笑靥迎人,似欲点头问我别来无恙也。才过五里亭,苍林荟蔚,香草缤纷,数树桃花,娇憨可掬。回忆十年前,老梅数株,高出檐屋,今都就槁。寺僧易种以桃,千红斗艳,几疑武陵源尚在人间也。然余性爱梅,不爱桃,转瞬数年,景象一变,可以觇世态之沧桑矣。日午,入涌泉寺,随山僧啖蔬饭,既饱,摩娑四壁,旧题漫灭,不可复得。忆少时与吾友石生、霁泉雅集于此,浩歌狂啸,击碎唾壶,意气豪迈,不可一世。曾几何时,风流云散,霁泉墓木已拱,石生浪迹欧州,欲得再与把臂,付之梦想而已。
兹山终古不改,得于十年后,使余重游旧地,人缘虽悭,名山之福犹获再享,亦幸事也。是夜辗转不寐,和尚云印极道绝顶胜景,邀余出游,允之。夜半首途,阴雾迷漫,咫尺莫辨。攀危岩,披茸草,蹀躞于磊砢中,约十余里,至朱晦翁所题“天风海涛”处,有亭翼然,颜曰:“观日”。惜为时太晚,日驭已徘徊于空际矣。俯视四野,群山如丸,千林若荠,行云奔逃,疾如飞鸟。宿霭作雨,忽阴忽晴,碧海接天,一色莫辨。近岩松涛怒吼,气象萧森,拉杂尘心,到此悉寂。下方缕缕炊烟,时已傍午。乘兴而下,抵喝水岩。复与方外群僧,纵谭琐事,但彼辈无风雅者,殊觉可厌耳。
次早,得邮书,促赴芜湖,匆匆行迈,山灵有知,当为扼腕。倘天假之缘,数年后,得与石生再来一游,想亦山灵所深许。然使天或靳余英年,抑或靳我石生,不使再见,即再见,或不能携手重游旧地,因在意料中也。譬如半山亭之梅,悉变为桃,梅之福宁不及桃,而竟不及桃,安知桃之后,不有他树为之代庖乎?余之能否再游兹山,亦犹之梅与桃也。嗟呼!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舟次无聊,挥毫记之,亦聊以志感云。
《陈烈士勒生遗集》卷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南京印本
郁达夫(1896~1945年)浙江富阳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小说《沉沦》等,散文主要游记,文笔优美。抗日战争时,在南洋群岛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后在苏门答腊,为日军所害。
游鼓山记
(一)
周亮工的《闽小记》,我到此刻为止,也还不曾读过;但正托人搜访,不知他所记的究竟是什么,以我所见到的闽中册籍,以及近人诗文集子看来,则福州附廓的最大名山,似乎是去东门一二十里地远的鼓山。闽都地势,三面环山,中流一水,形状绝像是一把后有靠背,左右有扶手的太师椅子。若把前面的照山,也取在内,则这把椅子,又像前面有一横档,给一二岁的小孩坐着玩的高椅了。两条扶手的脊岭西面一条,是从延平东下,直到闽侯结脉的旗山;这山隔着江水,当夕阳照得通明,你站上省城高处,障手向西望去,原也看得浓紫氤氲;可是究竟路隔得远了一点,可望而不可即,去游的人,自然不多。东面的一条扶手本由闽侯北面的莲花山分脉而来,一支直驱省城,落北而为屏山,就成了上面有一座镇海楼镇着的省城座峰;一支分而东下,高至二千七八百尺,直达海滨,离城最远处,也不过五六十里,就是到过福州的人,无不去登,没有到过福州的人。也无不闻名的鼓山了,鼓山自北而东而南,绵亘数十里,襟闽江而带东海,且又去城尺五,城里的人,朝夕偶一抬头,在无论甚么地方,都看得见这座头上老有云封,腰间白樯点点的磈奇屏障。所以到福州不久,就有友人,陪我上山去玩,玩之不足,第二次并且还去宿了一宵。
鼓山的成分,当然也和别的海边高山一样,不外乎是些岩石泥沙树木泉水之属;可是它的特异处,却又奇怪得很,似乎有一位同神话走出来的艺术巨人,把这大石块、大泥沙、以及树木泉流,都按照了多样合致的原理,细心堆叠起来的样子。
坐汽车而出东城,三十分就可以到鼓山脚下的白云廨门口:过闽山第一亭,涉利见桥,拾级盘旋而上,穿过几个亭子,就到半山亭了;说是半山,实在只是到山腰涌泉寺的道路的一半,到最高峰的屴崱————俗称卓顶————大约总还有四分之三的路程。走过半山亭后,路也渐平,地也渐高,回眸四望,已经看得见闽江的一线横流,城里的人家春树,与夫马尾口外,海面上的浩荡的烟岚。路旁山下,有一座伟大的新坟深藏在小山怀里。是前主席杨树庄的永眠之地;过更衣亭、放生池后,涌泉寺的头山门牌坊,就远远在望了,这就是五代时闽王所创建的闽中第一名刹,有时候也叫作鼓山白云峰涌泉院的选佛大道场。
涌泉寺的建筑布置,原也同其他的佛丛林一样有头山门,二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后大殿、藏经楼、方丈室、僧寮客舍、戒堂、香积厨等等,但与别的大寺院不同的,却有三个地方。第一是大殿右手厢房上的那一株龙爪松;据说未有寺之先,就有了这一株树,那么这棵老树精,应该是五代以前的遗物了,这当然是只好姑妄听之的一种神话,可是松枝盘曲,苍翠盖十余丈周围,月白风清之夜,有没有白鹤飞来,我可不能保,总之,以躯干来论它的年纪,大约总许有二三百岁的样子。第二,里面的一尊韦驮菩萨,系跷起了一只脚,坐在那里的,关于这镇坐韦驮的传说,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现在只能含混的重述一下,作未曾到过鼓山的人的笑谈,因为和尚讲给我听的话,实际上我也听不到十分之二三,究竟对不对,还须去问老住鼓山的人才行。
从前,一直在从前,记不清是哪一朝哪一年了,福建省闹了水荒呢也不知道旱荒,有一位素有根器的小法师,在这涌泉寺里出了家,年龄当然还只有十一二岁光景。在这一个食指众多的大寺院里,小和尚当然是要给人家虐待奚落、受欺侮的。荒年之后,寺院里的斋米完了,本来就待这小和尚不好的各年长师兄们,因为心里着了急,自然更要虐待虐待这小师弟,以出出他们的气。有一天雨风雷鸣的晚上,小和尚于吞声饮泣之余,双目合上,已经矇眬睡着了,忽而一道红光,照射斗室,在他的面前,却出现了那位金身执杵的韦驮神,他微笑着,对小和尚说,“被虐待是有福的,你明天起来,告诉那些虐待你的众僧侣吧,叫他们下山去接收谷米去;明天几时几刻,是有一个人会送上几千几百担的米来的。”第二天天明,小和尚醒了,将这一个梦告诉了大家,大家只加添了些对他的揶揄,哪里能够相信?但到了时候,小和尚真的绝叫着下山去了,年纪大一点的众僧侣也当作玩耍似的嘲弄着他而跟下了山。但是呀!前面起的灰尘,不是运米来的车子么?到得山下,果然是那位城里的最大米商人送米来施舍了。一见小和尚合掌在候,他就下车来拜,嘴里还喃喃的说:“活菩萨、活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的财。”原来这一位大米商,因鉴于饥馑的袭来,特去海外贩了数万斛的米,由海船运回到福建来的,但昨天晚上,将要进口的时候,忽而狂风大雨,几几乎把海船要全部的掀翻,他在舱里跪下去热心祈祷,只希望老天爷救救他的老命,过了一会,霹霹雳一声,榄杆上出现了两盏红灯,红灯下更出现了那一位金身执杵的韦驮大天君。怒目而视,高声而叱,他对米商人说:“你这一个剥削穷民,私贩外米的奸商,今天本应该绝命的:但念你祈祷的诚心,姑且饶你,明朝某时某刻,你要把这几船米的全部,送到鼓山寺去,山下有一位小法师合掌在等的,是某某菩萨的化身,你把米全部交给他吧!”说完不见了韦驮。也不见了风云雷雨,青天一抹,西边还出现一规残夜明时的月亮。
众僧侣欢天喜地,各把米搬上了山,而小和尚走回殿来,正想向韦驮神顶礼的时候,却看见菩萨的额上,流满了辛苦的汗,袍甲上也洒满了雨滴与浪花,于是小和尚就跪下去说:“菩萨,你太辛苦了,你且坐下去歇息吧!”本来是立着的韦驮神。就突然地跷起了脚,坐下去休息了。
涌泉寺的第三特异之处,真的值得一说的,却是寺里宝藏着的一部经典。这一部经文,前两年日本曾有一位专门研究佛经的学者,来住寺影印,据说在寺里寄住工作了两整年,方才完工,现在正在东京整理。若这影印本整理完后,发表出来,佛学史上,将要因此而起一个惊天动地的波浪,因为这一部经,是天上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藏,就是在梵文国的印度,也早已绝迹了的缘故。此外还有一部血写的金刚经,和几叶菩提叶画成的藏佛,以及一瓶舍利子,这也算是这涌泉寺的寺宝,但比起那一部绝无仅有的佛典来,却谈不上了。我本是一个无缘的众生,对佛学全没有研究,所以到了寺里,只喜欢看那些由和尚尼姑合拜的万佛胜会,寺门内新在建筑的回龙阁,以及大雄宝殿外面广庭里的那两枝由海军制造厂奉献的铁铸灯台之类,经典终于不曾去拜观。可是庙貌的庄严伟大,山中空气的幽静神奇,真是别一境界,别一所天地;凡在深山大寺如广东的鼎湖山,浙江的天目山,天台山等处所感到的一种绝尘超世,缥缈凌云之感,在这里都感得到,名刹的成名,当然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三月在福州
(二)
《福建通志》的山经里,说鼓山延袤有数十里长,所以鼓山的山景,决不至只有几处;而游览的人,也决不是一个人在山上住几天就逛得了。不过涌泉寺全山的一个中心,若以涌泉寺为出发点而谈鼓山,则东面离寺只有里把路远的灵源洞、喝水岩,以及更上一层的朱子读书台,却像是女子脸上的脂粉花饰,当能说是一山的精华荟萃的地方。
到灵源洞的山路,是要从回龙阁的后面经过,延山腰一条石砌小道,曲折而向东去的。路的一面就是靠小顶峰的一面,是铁壁似的石崖,在这一排石崖里,当然还有些花草树木,丛生在那里,倒覆下来成了一条甬道。另一面是一落千丈的山下绝壑了;但因为在这绝壑里,也有千年老的树木生长在那里,这些树顶有时候高得和路一样平,有时还要高出路面一二丈长,所以人在这一条路上走路,倒还不觉得会发什么寒栗,彷佛即使掉了下去,也有树顶树枝,会把你接受了去,支住你的身体似的。不过一种清幽,清閟的感觉,却自然而然在这些大树,绝壁、深壑里蒸发出来,在威胁着你,使你不敢高声说一句话。
山径尽处,是一扇小小的门;穿门东望出去,只是一片渺渺茫茫的天与海,几默树梢,或一角山岩,随你看的人所立的角度方位的变移,或有会显现一下,随即隐去,到了这狭狭的门外,山路就没有了,没有路怎么办呢?你且莫急,小门外的百丈谷中,就是灵源洞底了;平路虽则没有,绝高绝狭的下坡石级,自然是有的。下了这一条深深的石级,回头来一看高处,又是何等耐人寻味的一幅风景!石级的狭路,看过去象是一条蛇的肚皮,回环曲屈,夹盘在绿的树,赭黑色的岩石的中间,在这层层阴暗的石树高头,把眼睛再抬高几分,就是光明浩荡的一线长天了。你说是这景致,还不够人寻味么?
下了石级,我们已经到了灵源洞底了,虽说是洞,但实际却不过是一间天然的石屋。平坦的底,周围有五六丈方广,当然是一块整块的崖石。而在这底的周围、中部,以及莫明其妙的角落里,都有很深的绝涧,包围在那里。下石级处,就是一条数丈深的石涧,不过在这石涧上面,却又架着一块自然的石桥,站在石桥上,朝西面桥下石壁一看,就看得见朱夫子写而刻石的那一个绝大的“寿”字,起码总要比我们人高两倍,宽一倍的那一个“寿”字。
洞的最宽广处,上面并没有盖,所以只是一区三面有绝壁,前面是深坑的深窝。崖石、崖石、再是崖石;方的、圆的、大的、小的,象一个人的、象一块屏风的、象不知甚么的,重重叠叠、整整斜斜;最新式的立体建筑师,叠不到这样的适如其所。《挑滑车》的舞台布景画,也画不到这样的伟大;总而言之,这一区的天地,只好说是神工鬼斧来造成的,此外就没有什么话讲了。可是刻在这许许多多石头上的古代人的字和诗,那当然是人的斧凿;自宋以后直到现在,千把年的工夫,还没把所有的石壁刻遍;不过挤却也挤得很,挤到了我不愿意一块一块地去细看它们的地步。
洞的北面靠山处,有一间三开的小楼造在那里;扶梯楼板,有点坏了,所以没有走上去。小楼外的右边,有一块高大的崖石立着,上面刻的是“喝水崖”的三个大字,故事又来了,我得再来重述一遍古人脑里所出来的小说。
《三山志》里说:“建中四年,龙见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胄曰,神物所播,宜建寺以镇之。后有僧曰灵峤,诛茅为台,诵《华严经》,龙不为害,因号曰华严台,亦以名其寺。”照这纪事看来,寺原还是古洞,而洞却以龙灵,所谓华严台,华严寺,也就在这洞的东边,不过“喝水崖”的三字,究竟是不是因这里出了龙,把水喝干了,于是就有此名的?抑或同一般人之所说,喝水之喝,是棒喝之喝,盖因五代时神僧国师晏,诵经于此,恶水声喧轰,叱之,西涧乃涸,并流于东涧,后人尊敬国师,因有此名?我想这个名目的由来,很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现在大家都只晓得坚持后一说,说是经国师晏一喝,这儿的洞里的水就没有了,并流到东涧,但我想既要造一个故事出来,何不造得更离奇一点,使像安徒生的童话?一喝而水涸,也未免太简单了吧?
经过这灵源洞后,再爬将上去,果然是一个台,和一个寺;而这寺的大殿里,果然有一条水,日夜在流,寺僧并且还利用了这水,造了一个小小的水车,以绳的一端,钓上水车,一端钓上钟杵,制成了一个终年不息的自然撞钟的机械。而这一条水的水质,又带灰白色的而极浓厚,像虎跑、惠山诸泉,一碗水里,有百来个铜子好摆,水只会得涨高,决不会溢出。
在这寺门前的华严台————也不知是不是————上,向西南了望开去,已经可以看来见群峰的俯伏,与江流的缭绕了,但走过石门,再升上一段,到了山头突出的朱子读书台去一看,眼界更要宽大,视野更要辽阔。我以为在鼓山上的眺望之处,当以此为第一。原因是在它的并不象屴崱峰的那么高峻,去去很容易,而所欲望见的田野河流山峰城市,却都以在这里看得明明白白。我的第二次上鼓山,是于黄昏前去,翌日早晨下来的;下山之先也攀上了这一处朱夫子读书的地方。同游的人,催我下山,催了好几次,我还有点儿依依难舍,不忍马上离去此二丈见方的一块高台。坐上了山轿,也还回头转望了好几次,望得望不见了,才嗡嗡念着,念出了这么的几句山歌:
夜宿涌泉云雾窟,朝登朱子读书台。
怪他活泼源头水,一喝千年竟不回。
实在也真奇怪,灵源洞喝水崖前后左右的那些高深的绝涧里,竟一点儿流水也没有,我去的两次,并且还都是在大雨之后,经过不久的时候哩。
鼓山的最高峰名屴崱峰,卓顶峰,状如覆釜,时有云遮;是看日出,看琉球海岛的胜地我不曾去。大顶峰北下,是浴凤池;据说樵者常见五色雀群,饮浴于此。池之南有石门砑立;应真台、祖师崖、涌泉窦、甘露松、白猿峡、香炉峰,都在石门之右。浴凤池右下,走过数峰,达海音洞,洞口宽大,有好几张席子好铺;其中深不可测,时闻海音,所以有此名称。白云洞在海音洞下,由黄坑而登,只有一里多的山路,险巇峻峭,巨石如棋散置路上。听老游的人来说,鼓山洞窟,当以白云洞为第一;但这些地方,我都还不曾亲到,所以夸大的话也不敢说;迟早总想再去一趟的,现在暂且搁在一旁吧。此外的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狮子峰、钵盂峰……峰……崖之类,名目虽则众多,但由老于游山者看来,大约总是大同小异的东西,写也写不得许多,记鼓山的文字想在此终结了。
按:本文(一)为《闽游滴沥之二》、(二)为《闽游滴沥之三》的一部分,原文略有删节,题目亦编者所加。
何敏先字茗仙,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福州师范学校毕业,曾在县教育局任职,苦学喜游,走遍全省各县。不幸早年逝世。
八游鼓山印象记
福州市鼓山景色不但是福建省十二名胜中首屈一指,即在全国许多胜迹中,也可算是负有相当盛名。兹就我个人十载以来八度登山、遨游所得的印象,与参考旧志及近代作家们所写关于她的游记,加以分门别类,作个有系统的介绍,使今后游石鼓者虽无山僧引导,亦能按图索骥,得个粗线条的轮廓而归。
悠久的历史
考鼓山建寺的历史,相当悠久。其先白云峰下原为一潭,毒龙居之,每兴风雨,损人禾稼。唐建中四年(783年)龙现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胄请僧灵峤诛茅为屋,诵《华严经》于潭旁,龙来听经,久之,自行他徙,因奏建寺,号曰“华严台”。五代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王审知填其潭为寺,并往雪峰邀请僧神晏主持,号“国师馆”。其后,宋真宗赐额“鼓山白云峰涌泉院”,明永乐五年(1407年)改为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毁于火,僧遂迁居廨院。万历间,僧月江等营静室以居。天启七年(1627年),僧道瑞、宏晓任兴造之事。请博山无异大和尚住持之。清顺治初,僧元贤重修,如是兴而复废,废而复兴,凡有几度,及历年来时加修葺,故迄今寺貌结构,仍能保持当日的庄严堂皇。
登山的前奏
廨院上山到涌泉寺行程约长十里,并历经七亭及二千五百零五级的石阶(按:陈文涛说三千八百九十五磴),好在石阶都是宽阔平铺,且数级一坦途,里许一小亭,屈曲蜿蜒,状如羊肠。夹道茂松翠柏,涧壑潺潺流泉,实在在引人入胜,虽迈步登山,亦不为劳。抗战前,省会公安局于廨院设有鼓山管理员,将附近各乡村原有的竹舆(俗呼兜,可供营业用者),选择六十乘,舆夫一百二十名,预备夫六十二名,专供游客挑行李及添雇抬舆之用,而舆之制造极简单,仿如桥式,上覆活动白色布蓬罩,以蔽风日,并编定号数及舆夫服装标识,使游者益增便利舒适,所需代价仅一二元。在抗战期中,抬舆价上山非百元不可,下山还较便宜一半,健行者还是缓步登山为妙(按:解放后,汽车由公路可直通寺门,无须步行,而下列七亭,亦成为陈迹,但七亭沿途俱系名胜、碑刻所在,不容阙载,故仍存录,藉可看出鼓山今昔的变化)。
松篁十里间
到了廨院,最先映入我们眼帘,就是路旁“闽山第一坊”。她系宋僧德融建的,初名“通霄”,后以朱晦翁书“闽山第一”四字揭眉,遂改今名。过此五十武,经利见桥,有“瑞泉”与“祝圣万年碑亭”在对面白墙边,中横长方形石碑一块,上刻“祝圣万年亭”五字。从这里左转,即“白云廨院”,该院乃用以安行僧、办道粮及云水宾客之往来,为涌泉寺之化城,与寺同时建。其中大殿多古佛,后面系法堂。对门“南园”内有“普贤殿”,中多杂树。院左十武,流水一弯,上架以石,名“东际桥”,亭名“东际亭”。登阶六级为平地,走十步,上三十三级,又是平地,如是十步三级,八步三十八级,一百六十六步四级,八步三级,八步十级,共九十九级,始抵第一亭。
(一)第一亭————仰止亭,即观音亭。山下到此计登九十九级,亭的建筑极平凡,四面皆空。此时山上岩上的石刻,亦从此开始呈现于吾人眼。傍于道右,有一片硕大平铺的岩壁,镌上不少名人题字。首先为清福州知府李拔书“声满天地”及前私立三山中学校长周靖书“去私救国”。再登上四十六级间,沿途乃有不知为何人所书的“东障鹏霄”、“云程发端”等字。过此,为前闽侯县政府当民十九(1930年)那年,为保护“名山禅林”的布告,全文简短数十言,刻在石上。接着就是萧梦馥书的“青山绿林”。走过这一段石级,道左有“洗心台”,台为岩石,形如人心,下面水声潺潺。附近阶旁有条石椅,供人一憩。从这里起,在亭与亭之间,每相距不远,都有同样石椅设备。再缓步而登一百六十六级,便至一石屋,即为第二亭(沿途石刻共计十处)。
(二)第二亭————俗称头亭。第一亭到此,计登三百六十七级,山下到此,共四百六十六级。亭内空无所有,前后辟两门,以通上下往来。左右有围墙围着,壁间嵌前闽侯县长欧阳英书“听涛观瀑亭”五字。越过此亭,登上二百七十一级至第三亭(沿途石刻只有一处)。
(三)第三亭————即乘云亭。第二亭到此,计登二百七十一级,山下到此,共七百三十七级。该亭俗呼“水亭”,初名“梯云”,后因亭旁有泉曰“灵泉”,故又名“灵泉亭”。亭中题有“愿登觉岸”四字,附近有宛平县弟子那福书“七佛师”。又上一百四十九级间,沿途石刻有“空色相”、“现五蕴光明”、“大慈悲度一切苦厄”、“卓尔”、“乘云”(王用文书)、“高坚在望”、“维行”(平潭陈魁梧书)等字。抵此又有条石椅,再登三百四十五级,这段中途石刻,计有“南无阿弥陀佛”、“仰涛”、“尚远”、“天风吹梦”、“风怒涛飞”(不知何人所书,笔力雄劲有神)、“小鼓”(高鹤楼书)、“南无阿弥陀佛”、“半山”(表示走到此处,才抵半山。),转瞬间即抵第四亭,沿途石刻共十六处。
(四)第四亭————半山亭,第三亭到此,计登四百九十四级,山下到此共一千二百三十一级。该亭所以名“半山”,盖以亭在岺之半,故名,又称“合珪亭”,因有两石如合珪,故名。亭中有匾题“神皋奥区”及石佛塔一座。僧人在此设茶桌,卖糕饼,以招待游客。亭前空地陈列石桌、石椅。由该亭再连登三百四十七级后,道旁又有一条石椅,续登至八十三级时,先望“能通仙苑”石刻。路之右边有杨树庄墓碑亭,它为一现代化水泥钢骨建的凉亭,雕梁画栋,颇为华丽。杨乃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年)间福建省政府主席,死后葬此山上。其墓园即在亭之附近里许,墓碑系青石所琢,手工颇精,字乃汪精卫所题,后人以汪为卖国汉奸,将他名字毁坏,并画个乌龟以见弃之。又九十级过桃岩洞及五谷祠,即至第五亭,沿途并无石刻。
(五)第五亭————茶亭,第四亭到此,计登五百二十级,山下到此,共一千七百五十一级。游客到此,无不感觉足疲力竭,李拔在亭旁所书“欲罢不能”四字,命意殊深。亭的建筑规模,可算七亭之最,并有庵及佛像,陈设甚佳。堂上有达摩祖师壁书,据云:为一台湾美术家的杰作,全幅仅用毛笔蘸墨,绘于白色壁间,寥寥不及几十笔,十分传神。附近有舍利窟,亦名“茶园”,在香炉峰前。自山腰分径而入,别为一区,倚岩架屋,居民二十余家。传闽王创寺时,谪罪人于此,使之种茶,以供香积,即世所称之“鼓山半岩茶”。茶色香,风味佳,推为闽中第一。从茶园上去,沿途左右,石刻更多,几令人目不暇接。计所登三百三十级间,有“善哉”、“宜勉力”、“做好人,行好事,读好书,说好话”、“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云路”、“望奎楼”、一笔“寿”字,活跃如神龙飞舞,曾为人用墨拓去,当作中堂悬挂。“开窍星”、“蓬莱在望”、“莫作心头过不去之事”、“无量寿”、“南无阿弥陀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威音王佛”、“高山仰止”、“何修到”、“宝筏度人”、“南无无量寿佛”、“立念回天”、“作如是观”(南城渭卿胡印)、“毋息半途”、“天地正气”、“求真理”、“宏法利生”、“行良心”、“佛”(这个佛字写得非常笔化)、“河山冠冕”、“阿弥陀佛”、“慧日辉煌”等三十一处。看到这里,石阶亦告一段落。同时左边更现出一条小径,乃通往十八洞。正面缓步行一百零九步,杨树庄墓即可看到。又一百二十步,升上十级,走八十八步,再登十四级,有望云居士于光绪丁酉年(1897年)用口衔着笔书“静神养气”四字。再上二十级,先见古佛塔两座继到第六亭,沿途石刻共三十二处。
(六)第六亭————更衣亭(又名观化亭),这里距山门只有一里,传闽王审知上鼓山访异僧时,曾更衣于此。亭中有清杨庆琛对联:“开门曾仰前王节;入寺还更此寺衣”。附近有“五贤祠”。过此亭,又是坦荡石道,使人气爽,且沿途九十步间,石刻特多;如一笔“虎”、“白云沧海”、“道心坚固”、“云程”、“忘机”、“是胜因地”、“灵山岐岺”、“足以名志”、“今古名山”、“人海飞鸿”(下面另附诗一首)、“皆大欢喜”、“福城东胜”、“我无人相”(附诗一首)、“五蕴皆空”、“一壑风树”、“霖雨苍生”、“为善最乐”、“悟境”、“心”、“佛”、“提倡国货”、“忠孝廉节”(后学林可相敬录宋忠臣文信国公书,每字径约数尺,极为雄壮,有魄力)由此登上二百级有“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云磴松涛”、“草堂愿如”(附诗一首)、“心路须平”、“南无阿弥陀佛”、“宛如极乐”、“三民主义万岁”、“亦到涌泉”。至此登一百三十级后,即为一段斜坡。同时右边通往放生园,左通佛窟(乃一壁立巨岩,中刻经文)。正面再行四十步,下五十级,乃巨松夹道,苍翠欲滴的“万松湾”,国民政府蒋介石主席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莅榕游石鼓时,所题“其介如石”四字,即在此途中的左边岩上,因字体不大,很容易忽略。附近更有卢兴邦书“行仁义事”,及不知名所书“以进大同”等。该寺前代和尚塔数座(即海会塔)即造于此,最后为“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知足常乐”等处,沿途题字,欣赏至此,全部告终,统计共九十处。其中以第六亭至第七亭这段途中最多(共三十六处),第二亭至第三亭这段途中最少仅一处。再徘徊八十六武,即至山门的第一个牌坊,前额曰:“石头路滑”,后额曰“又恁么去”,过七十步,趁迎面那列短垣绕入,垣上壁间嵌一黑碑石,横书“入佛境界”。经香炉峰边(此峰在钵头峰东,为寺的前案,俗呼“阿弥陀佛”山),左转二十步,抵第七亭。
(七)第七亭————驻锡亭,即最后一个亭。第六亭到此,计登三百八十级(其中最后五十级系向下走,盖地势至此,又低落下去),及二百九十二步(分三段),山下到此,总计二千五百零五级。向此亭直穿下去,系通往灵源洞。亭右左壁,有福州名画家李霞画的佛一帧,颇活跃神妙。亭左正面,乃鼓山山门,门额之上直书“无尽山门”(此乃山门旧址,古额为无尽门),左右石柱对联的佳句写着“通霄路远尘氛尽;无尽门开法界宽”。又左右所悬木板联句,是“石点头,虎甘受戒;鼓晨钟,龙来听经”。门左右大石柱刻着“振刷精神功参妙谛;光明磊落法证菩提。”(此联系前福建省高等检察厅厅长邱在元题,又左右前柱刻着“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另一付木板对联写着“门纳海天宽,披残碧汉,浮云万里空中参富贵;钟敲山月落,唤醒黄粱,大梦一番见后薄公侯。”(宁化名书家伊秉绶之子宗陶所题)句法雕琢极精,读之有味。跨入山门,后面左右两柱对联:(1)“弘菩提之愿;开入圣之门。”(台湾李盛福题),(2)“石鼓浮海岛;灵泉涌寰宇。”(台湾女信士林朝姑题)对面墙边有石龛,中竖石刻“南无阿弥陀佛”,两边小柱对联刻“顶上月光高屴崱;指头甘露沛锦江。”从此龛前,循曲径行一百三十武,至第二个牌坊,前额曰“万福来朝”,后额曰“回头是岸”。楼之右边即迥龙阁,过此牌坊又是一弯,走百余武为第三个牌坊,前额写“海天砥柱”(前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书),后额写“佛圣门庭”,拾级登两石阶,过十数武,为罗汉泉(相传有僧来此,以手指地,而泉水忽上涌,故名。寺之称涌泉,典故即出于此),泉口四方形,旁有石牌,刻着“罗汉泉”,径约一尺,迎面即庞大的广场(这个广场系用雪白的石条砌成斜度,别饶风趣)与巍峨壮观的涌泉寺。
痛心一回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