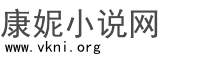马月猴年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康妮小说网https://www.vkni.org),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华夏古代王朝,如果削弱儒家,引入法家和墨家,使得儒家掌握『德治』主教化,法家制定『礼制』主律法,墨家注重『民本』主农工,在分出三个内核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建立起属于华夏自身的,全新的一种三权分立的政治阶级统治模式出来?
斐潜不知道能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但是他觉得可以试验一下。
三权分立,并不是西洋独有的概念。
华夏古代就有,但是也和后世的近现代的三权分立有很大的区别。
周朝就有『三监』制度,甚至试图用祭祀权牵制行政权,以史官监督形成当代事功加上历史评价的双轨制约,但是最终么,还是被周公推行的制礼作乐的体系所吸收。
汉代也同样形成了三角形的博弈。皇帝和中外朝之间,然后加上了御史系统,不过也很显然这种三角形在皇权独大的情况下导致双边不稳。
在唐朝,以及唐朝之后,其实统治阶级的中间管理层已经意识到皇权过大导致的危害性,连皇帝本人也心知肚明这一点,所以英明的皇帝都会有意识的抑制个人情绪,而偏向于理性的,多角度的解决国事之中出现的问题。
比如唐朝就出现了五花判事,宋朝的中书门下枢密院,明朝的内阁六部九卿等等……
但是华夏的三权分立,或者说类似于三权分立的维度和西方是有差异,也有相同点的。
首先华夏的权力来源,是从所谓上古时期的神秘天命,转变成为周朝的祖宗血统,然后再到改变血统也可获得的天子传承,可以看出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传递脉络,而对于西方来说,更像是原始部落的合议推选,横向之间的选择一个老大来当头。
其次,因为其本身的来源不同,也导致了政治制度的目的不一样。纵向的华夏权力,第一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王朝的稳定,子传孙万万代。虽然谁都知道这不可能,但是谁都想要多传几代。而西方主要就是利益保障,选取某人当老大,是因为某些利益的交换,当有新的利益出现的时候,随时可以换老大。
最后,在华夏和西方的各种表面特征,权力机构名称,分管职能不同等等现象的掩护之下,但是实际上其核心本质都是利益,或是权柄的争夺。
不管是华夏的纵向权威,还是西方的横向契约,都是可以归纳为一点,独裁,或是垄断,必然会出问题。而追求垄断,或者叫做大一统,又是每一个公司,组织,国家等等的必然追求。
斐潜认为,将皇帝扯下来自己坐上去,那么无疑是将自己主动置放于旧有的轮回体系之中,屠龙勇士转职成为恶龙,然后等待下一个屠龙勇士的到来。
或许三五百年,或许时间更短。
所以斐潜就设想,华夏古代王朝如果削弱儒家,同时引入法家和墨家,分别让儒家负责德治和教化,法家制定礼制和律法,墨家注重民本和农工,然后推衍这样的制度,会有什么演变,及其对古代华夏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意义?
斐潜一度想过,要约束皇帝的权力,但是随后他在青龙寺的建设和讨论的过程当中发现,实际上华夏之中,还有一个隐形的皇帝,那就是儒家。
于是斐潜就开始思考,如果历史上儒家没有成为主导思想,而是与其他学派结合,华夏的发展会有何不同。
有了这样的前提,斐潜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希望能有一个系统的推衍,包括制度演变的具体阶段、各学派的分工协作、可能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对华夏后续经济、科技、社会结构的影响。
于是乎,斐潜就回顾了历史上的儒家、法家、墨家的核心思想,以及它们在实际历史之中产生的影响。
墨家几乎是被法家和儒家等,再加上统治阶级联手干掉的。
毕竟原本墨家的思想实在是太超前了……
即便是在后世,普通的百姓也谈不上什么自由平等,需要普通百姓卖命的时候,大爷大伯大婶子叫得一个亲切,然后转头就是拿着针管准备来一针,表示这是『刺激』政策,就像是给牛马抽血注射兴奋剂一般。
在华夏古代民智不高的情况下,墨家是必须要改的。
民本和农工,显然更加适合墨家的定位,并且也不会太超前以至于扯到蛋。
法家么,在秦朝的应用还是很成功的,只不过是类似于后世的军事管制之下的计划经济,在战争暂停期间,就无法跟上百姓生活的需求,强行压制必然就是嘭一下,宛如高压锅爆炸了。
在墨家彻底被敲死,法家被一杆子扫下船之后,笑到最后的当然就是儒家。
儒家捡起了留在船上的墨家和法家的包裹,然后扔掉了包裹皮,将法家和墨家的东西,藏到了自己的袖子里。所以,将儒家拆分出来的前提条件,也是具备的,毕竟儒家之中有一些东西原本就是其他学派的。
因此,斐潜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变成了三个学派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如何?
又如何避免冲突?
比如,法家重法律和集权,墨家强调平等和实用,儒家注重道德教化,这三者可能在统治方式上有矛盾的时候,要如何调和?
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仁政德治如何调和?
墨家的民本和农工可能会推动科技和手工业发展,但古代中国重农抑商,这是否会改变国家的农业的根本?
如此,等等。
而且斐潜还需要考虑这种制度演变的不同阶段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比如在初期,可能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权力之间覆盖冲突的不多,分工也比较明确。然后到了中后期,就出现了三不管地带,亦或是有油水的大家都想要抢,权利争夺之下演变成为制度崩塌。
三者对外的时候无往不利,但是三者对内的时候,就像是在演武堂的拆台,也是同行才知道毒手应该下在何处。
土地兼并是王朝衰败的主因之一,所以斐潜又需要重新设计土地制度。
要限制土地集中,促进公平分配。
单纯的将土地回收,然后下发给普通的百姓民众,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因为百姓民众是会增加的,而土地的增速,不管是哪朝哪代都是远远小于人口的增速,因此在所谓分发给屯田户,或是自由民等方式,只能在建国初期人口稀薄的情况下进行,稍微过个几十年,土地分发制度肯定就会崩坏。所以解决的办法就两条,一条是土地完全国有化,另外一条就是定期重新分配,但是这两条路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官僚腐败是关键。
然后为了减缓和监督官僚的腐败,三家分权的内部竞争就可以成为相互去除病灶的一种手段。
同时三家分权确保权力制衡,也可以防止任何一方独大,但是这又需要有超出三家分权的上级机构,最高首脑,比如皇帝,或是丞相进行平衡或是裁决。
斐潜觉得,丞相或许会比皇帝好一些。
而要让三家都有机会担任丞相职务,就必须尽可能的平衡选举选拔机构,比如进行科举制的改革,让不同学派的人进入官场的数量大致相当。
这一点又要求了官僚数量会比分立之前要多很多,所以经济上面就要保证帝国官僚运作体系的费用足够支出,也就需要发展工商业,减轻农业负担,促进经济多元化。墨家的技术推动和法家的法律规范可以促进手工业发展,保障商业的有序,也反过来减少了对土地的依赖。
财政制度方面,避免传统的农业税为主,可能需要货币化税收,建立稳定的财政体系,防止财政崩溃。墨家的量化分析可能帮助预算管理,儒家和法家道德监督律法监察用来防止腐败。
军事方面,保持防御性力量,防止军阀割据,墨家的城防技术和法家的军功制度结合,同时儒家的教化减少内部叛乱,以及对外的文化侵袭。
文化方面,维持儒家教化,但融合法墨思想,促进实用主义和道德的结合,防止思想僵化。
要在华夏古代王朝之中,构建出可持续的政治制度,就需突破传统王朝的『土地=权力』绑定机制,建立动态均衡系统……
千头万绪,而落在笔端的,可能就是一条条简单的律令。
『着令。』
斐潜和庞统商议到了后面,便是基本上理清楚了一些思路,然后开始布置起来。
『参律院重修《九章律》,编大汉法典。不求律法完美,只求有例可循。以十年为期,添补增删。另设「明法台」,归于参律院之下。以类讲武堂,专述法例,巡判陈案,以平冤屈,复清明。』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